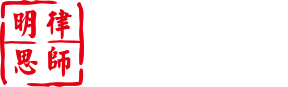


几乎所有的刑辩律师都曾在辩护词中援引“疑罪从无”原则,但最终被法院采纳的很少。从笔者办理多起相关刑事案件的经验来看,造成两者极大落差的原因是多元的,主要源于辩审双方对该概念的不同理解:疑罪的判断首先是一个事实问题,然后才是法律问题,而事实判断又是一个相对主观的标准,导致疑罪从无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
一、疑罪从无的概念
在中国法的语境中,疑罪从无是指证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尚未达到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推定为无罪的情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三款的规定,合议庭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此为我国法律关于疑罪从无原则的主要规定。
从刑诉法的相关表述来看,疑罪并非毫无证据作为指控基础的犯罪案件,而是有一定证据但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案件。疑罪之所以从无(而非从轻),与我国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密切相关。根据我国刑诉法的表述,刑事案件定罪标准应为“证据确实、充分”,具体而言,根据刑诉法第55条的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若案件证据未达到上述三个标准,则可以评价为“疑案”,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应认定无罪。
二、疑罪从无的两个极端:“幽灵抗辩”与举证责任倒置
疑罪的衡量标准为是否达到刑事案件“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司法实践中,辩护人为履行辩护职责常常对公诉机关的举证提出质疑。根据刑诉法的规定,该质疑只要达到使法官产生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的“合理怀疑”即可。所谓的合理怀疑,是指一个正常的理性人凭借生活经验对被告人是否犯罪所产生的一种怀疑。譬如,在故意杀人案件中,公诉机关已证明被告人甲在犯罪现场被抓获且有证人指控甲杀人,辩护人提出根据监控可知乙戴了面具于同一时间在现场附近出现,法官产生了被害人可能被乙杀害的合理怀疑。对辩护人的合理怀疑,若公诉机关未能提出新的证据加以排除,则该举证尚未达到刑事案件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应判决乙无罪。
不过,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何为合理怀疑仍存在各种不同的理解。在各种不同的理解中,“幽灵抗辩”与“举证责任倒置”可谓解读尺度的两个极端:
1、合理怀疑与“幽灵抗辩”。幽灵抗辩并非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学理上一般认为幽灵抗辩是指被告人一方针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提出的难以查实的抗辩,像一个似有似无、无法确证的“幽灵”。
幽灵抗辩与合理怀疑的区别在于,合理怀疑通常都有一定的理据(譬如有证据线索加以证明或者根据常理可以推断),而幽灵抗辩大多表现为一种主观的臆测。当然,幽灵抗辩与合理怀疑并无绝对的界限。譬如,在警方于被告人家中查获大量毒品但被告人声称毒品非自己所有的案件中,被告人的抗辩一般会被认为是“幽灵抗辩”而不被采纳,但如果被告人能提供相关的证据线索证明毒品为他人持有(譬如毒品被查获的地点正是朋友借宿的房间),则“幽灵抗辩”有可能被评价为一种“合理怀疑”。若公诉机关未能通过举证排除毒品为被告人朋友所有的合理怀疑,则被告人可能被宣告无罪。当然,最终是否认定其无罪,仍要结合证据的总体情况综合进行判断。
司法实践中,以“疑罪从无”为由提出的无罪辩护之所以难以被法院采纳,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当辩护人提出基于某一事由可以产生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的合理怀疑时,法官往往认为此抗辩属于幽灵抗辩。当然,法院直接在判决中论证辩护人的抗辩属于“幽灵抗辩”的情况比较少见,而通常代之以“现有证据足可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辩护人的辩护理由缺乏证据、不合常理”等表述。
2、合理怀疑与举证责任倒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9条的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此为公诉方承担举证责任的主要依据。上述提及,合理怀疑的成立依赖于常理或者一定的证据线索,当合理怀疑依赖于被告人一方提供的证据线索时,举证责任似乎由公诉人一方转移到了被告人一方。若果真如此,无疑是对“公诉机关承担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被告人一方不承担证明其无罪的证明责任”的一种严重违反。
笔者认为,被告人一方须对合理怀疑提供证据线索并不意味着举证责任的倒置。实际上,举证责任的承担存在限度,并由证明标准所决定。以民事诉讼为例,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应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一方承担对其特定主张的举证责任,其举证限度即为优势证据标准。当其提出的证据已经达到优势证据标准时即宣告完成了举证责任。此时,另一方当事人若想推翻该项主张,则须提供相应的依据,若无法提供即应承担败诉的风险。与此类似,刑事案件中公诉机关的举证责任也以证明标准为限,当公诉机关的举证已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时,即宣告举证责任暂时完成。此时,被告人一方若主张无罪,则须通过相关的举证或说理推翻原已确实充分的证据体系。若被告人一方举证不能,则法院将判决其有罪;若被告人一方的举证足以使法官产生合理怀疑,则说明当前的证据体系尚未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则举证责任又重新回到了公诉一方。若公诉一方未能进一步补强证据,则应承担被告人无罪的不利后果。显然,将证明标准纳入考察范围后,举证责任的承担并非一个绝对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不断往返、来回穿梭的动态过程。
三、疑罪从无的司法适用要点
疑罪从无作为一个法律推定是抽象的,若要使其从抽象的法律规定变成司法实践的指导规则,仍需在抽象规定与具体个案之间搭建类型化的适用规则。正如大法官沈德咏所言,“对于疑案,仅从概念上讲不枉不纵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为到了诉讼中,特别是司法审判这一最后阶段,无论是追求“不错放”还是“不错判”,都是两难的选择。”在这种两难抉择中须对疑罪从无作出某种妥协,并确立疑罪从无的底线。结合相关的理论及司法实践经验,可归纳出以下几个疑罪从无的适用要点:
1、疑罪从无与疑罪从轻的适用场景区分。一般认为,从疑罪从无到疑罪从轻是法治进步的一种体现,两高也在多个场合中也强调应摒弃疑罪从轻而坚持疑罪从无。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并非所有的疑罪从轻都必须禁止,须对疑罪从无与疑罪从轻的适用场景进行区分。
疑罪从轻一词出自东汉班固的《汉书·于定国传》,“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强调要体恤鳏寡孤独之人,对于不能确定构成犯罪的应从轻发落。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疑罪从无原则因其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即宣告有罪的做法无疑是值得批判的。现代法治国家一般认为,对于证据不能确证犯罪的情况应坚持疑罪从无原则,而非疑罪从轻。疑罪从无的适用,仅在证据不能完全证明重罪但可证明轻罪的情况下适用。譬如,在公诉机关指控甲构成受贿罪的案件中,现有证据仅能证明甲确有受贿事实但对于甲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存在疑问。此时,指控甲构成受贿罪这一重罪的主体证据不足,但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证据确实、充分,根据“疑罪从轻”的定罪规则可认定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这一轻罪。但是,倘若连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证据都不充分,则应坚持疑罪从无原则宣告甲无罪。
2、在任何情形中都应坚持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坚持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关键在于从证据裁判原则出发,保证法官不受外界其他的干扰并基于自由心证作出合乎法律的判决。从实践的情况来看,干扰司法工作者的适用疑罪从无原则的因素有几类:其一是“政治案件”的压力,判决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已为相关部门所决定,并通过行政层峰作用于经办人员。其二是“指标类”案件,即在某种特殊时期下基于办案指标的考量而对案件事实认定的证据裁判原则作出妥协。其三是司法系统内部普遍存在的责任追究压力,譬如在已批捕案件中若作出疑罪从无判决,则很可能意味着国家赔偿机制的启动。在法理上,此种压力虽只作用于检察机关,但由于公检法内部某种密切的联系,法院系统也将很快感受到此种压力。
上述所言都是导致疑罪从无原则难以被严格遵守的客观原因,但法官的主观因素对案件的认定也将产生重要影响,譬如,法官基于某种经验的判断可能认为某犯罪嫌疑人为累犯,而本次指控其犯罪的证据大概齐全,故认定其本次亦构成犯罪必然不冤枉。也有法官从“普遍贪腐”的观念出发先入为主地认为在职务犯罪中虽然客观证据缺乏,但认定某官员受贿必然与客观事实相符。譬如部分极端言论认为,“领导都贪,他那么大的领导只是指控受贿30万,必然不会冤枉他”……与客观的因素相比,此类主观因素主要是通过法官的自由心证间接作用于案件结果的,但无论如何皆与疑罪从无的原则有所冲突。
3、认罪认罚语境下的疑罪从无问题。2018修正的刑诉法通过国家基本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根据刑诉法第15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一般认为,即便是认罪认罚案件也不可降低刑事案件“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认罪认罚的案件法院将在审理时极大简化庭审流程,仅重点对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与量刑建议的合理性等进行调查核实。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作为刑事证据的一种,确实能够有力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在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情况下,很容易使公诉机关在提起公诉、审判机关进行审判时产生被告人有罪的自由心证。但是,由于法院在庭审过程中侧重点在于确定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真实性与量刑建议的合理性,对其他证据则缺乏足够的关注,案件证据是否已达“确实、充分”的标准仍然存在疑虑。故此,我们认为应强调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在适用认罪认罚制度时须仔细阅读案卷材料,对基本证据缺乏的案件不可以认罪认罚为由进行定罪,而应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不予起诉或者依法判决无罪。
4、重视客观证据的价值,并以客观证据为基础构建证据链。司法实践中,与“证据确实、充分”的类似表达有“定案的证据已形成完整锁链,可排除合理怀疑”。形成完整证据链的前提是证据之间可以互相印证并互相衔接,此为“证据印证模式”的应有之义。一般而言,证据之间互相印证并形成完整证据链即可保证实体的正确。但是,必须注意的是,以口供为基础的证据印证模式成立的前提是口供本身的真实性,一旦作为印证基础的口供真实性存在疑问,则该证据链将失去稳固的基础。以聂树斌案为例,原审有罪判决也是通过以口供为基础的印证模式作出的,但再审最终推翻了原审的有罪判决。根据1994年《石家庄日报的报道》,“干警们巧妙运用工薪战术……终于供述了拦路强奸杀人的罪行”,但日后的调查却发现本案无法排除刑讯逼供的可能性,并最终导致证据体系的崩塌。
笔者认为,运用证据印证模式时须对口供进行严格审查,避免将以刑讯逼供、诱供等取得的口供作为印证的基础。毕竟,一旦口供存在问题,其他客观证据也不是不可“伪造的”。在使用证据印证模式进行判断时,应尽量以客观证据,如书证、物证、视频等作为基础,并重点审查客观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对主要证据为口供或者口供本身存在疑问的案件,应谨慎地进行考察。综合全案证据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应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宣告无罪。